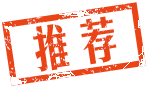|
|
明清之際,上海因得水上交通之利,日漸形成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黃浦江上船舶往來,十六鋪小東門外停靠著各幫商舟。凡是商賈雲集的場所,也總是百業俱興的地方。上海從一個濱海之邑,演變為繁盛之地,除了各業店舖林立之外,為商賈服務的行業如茶館、酒店、戲園,直至娼業也漸次發展了起來。
舊上海娼妓業的發展
若要在上海找尋娼妓最早的蹤跡,還得從“畫舫”說起。所謂畫舫,用最通俗的話來說也即是水上妓院。來滬操這營生的,多為蘇揚籍的秦淮娼妓。未開埠前的上海,既無火車,也無汽車等現代交通工具,有的只是在上海境內與黃浦江相通的蜿蜒數十里的吳淞江,正是這條江,成了她們賴以謀生的天然場所。
道光初年(1821年),上海的人口隨著商業的發展逐日增長。這時的娼妓業也從畫舫時代的水上轉而登岸來到陸上,上海縣城裏的虹橋左側便是娼妓最初駐足的地方。在將近三四十年的時間裏,各種名目的妓院鱗次櫛比地開設起來。來此冶遊的,主要是閩粵大賈。又如地處幽僻的梅家弄和鴛鴦廳側,也是煙花女子深藏的地方。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革命興起後,隨著租界的發展,上海的人口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增長。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從1855年的2萬餘人增加到 1865年的9萬餘人,法租界也增加了4萬餘人。這些人來自四面八方,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獲利後便尋歡作樂,這就促使城內的娼妓逐漸向城外遷移。另一方面,因戰爭的原因,來自江浙一帶的貧家婦女,為謀生計,許多人淪為娼妓。於是,租界裏的娼妓業也有了一次較大的發展,地點多在緊靠縣城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臨河一帶。太平天國革命結束後,租界內的富商又紛紛轉回內地,使上海的娼妓業受到很大的影響,幾乎要瀕於絕跡。
1856年前後,大批歐美殖民者來到上海,他們在這裡開設洋行、銀行和其他各種企業,從而產生了依附於洋人致富的買辦。據統計,自舊上海開埠至 1949年為止,上海的買辦已達萬人之數。這些買辦除了薪金之外,還有佣金和分紅的收入,有的年收入可達幾萬兩白銀,可算上海灘上除了洋商以外的最大闊佬。當時上海的一些地主、惡霸、軍閥、官僚等等階層的人,以種種手段搜刮錢財進行投機事業,往往也會在頃刻之間變成腰纏萬貫的富翁。這些家產以萬計算的人們,揮霍作樂的方式與洋人的跑馬、打高爾夫球和賽狗判然不同,而是以“金屋藏嬌”、“納妾嫖妓”為樂。他們月出數十金供美人開銷,這就使上海的娼妓業再度興盛。但是,這時的妓院並不設在租界內,而是又回到城內。清同光年間(1874-1875年),娼妓業最興盛的是老北門沉香閣一帶。因為當時這裡環境幽致冷然,而公共租界大馬路中,只有零星的低等居處,是不大會有人光顧的。至於原先臨河一帶因多係被視為低等的蘇北妓女,她們的營生主要是接船上的水手和洋行裏的西崽。被視為等級較高的蘇州、南京、上海籍的妓女,則多遷回老北門沉香閣一帶去接闊佬們了。
光緒初年(1875年)以後,上海租界日趨繁華,娼妓業隨著十里洋場的繁榮而與日俱增。根據1915年上海《中華新報》的調查,當時明娼僅公共租界一隅便達9791人之多,而數倍於此數的暗娼還不在此列。當時的公共租界人口總共約68萬餘,其中青壯年婦女約10萬餘人,這就是說每十幾個青壯年婦女中就有一個娼妓。如果再把法租界和華界中的娼妓人數作同樣的統計的話,這個數字可使今人為之咋舌。
這數以萬計的娼妓,由於來歷、籍貫、身分的不同,又可分為許許多多的種類和等級。歸納起來,大致有書寓、長三、幺二,以及最下層的臺基、野雞、花煙間、釘棚、鹹水妹、淌白、拆白黨……等等十多種。
舊上海娼妓等級
書寓
上海娼妓中等級最高的是“書寓”。書寓出現于清代咸豐初年(1851年),創始人名曰朱素蘭。朱善說書,並會填詞吟詩,她創設書場,挂上書寓的牌子,組織一些略有說唱技藝的女子從業。但這時期真正能與朱素蘭相比的書寓女子寥若晨星,因此聲勢並不大。到了同治初年(1862年),周瑞仙、嚴麗英在書寓中出了名,才使書寓名聲大噪,在娼妓業中佔居優勢地位。
早期書寓有嚴格的規則,進書場的娼妓須得有名師指點過方可掛牌,至少也須能唱上幾本傳奇的方可。書寓的娼妓號稱只賣藝而不賣身,除了說書彈唱,便是陪酒。陪酒時可與客人親近些,但喝完酒便須與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離,以示尊嚴。書寓的收入除書場的包酬外,一場書得大洋一元。書寓有時也出門陪酒,名曰出堂拆或出堂差。早期的書寓不賣淫則已,一旦賣淫,其身價高昂,遠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擔得了的。這只要從她們的穿戴和飲食起居上看便可見一斑。有些名妓手中一支鴉片槍,就價值千把元大洋。由於以上原因,當時書寓中的娼妓人數是很少的,主要是蘇、常、吳、揚籍,前去問津的也只是一些達官顯貴和他們的子弟而已。
光緒初年(1875年),書寓從城內向公共租界遷移,人數從100發展到300之多,大多分佈在公共租界的東西畫錦裏、百花底、桂馨裏、兆榮裏、兆華里、兆富裏、兆貴裏、尚仁裏、久安裏、同慶裏、日新里等弄堂中。她們為了保持書寓的地位,成立了書寓公所,規定入場唱說的須由公所批准承認資格。發展到後來,只需向公所納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塊書寓的招牌了。書寓中的娼妓多為蘇州、常熟、吳江、揚州籍女子,隨著人數的增多,她們往往互相傾軋。揚州幫最先被排斥,緊接著吳江幫也敗下陣來,最後在蘇常兩幫對峙的局面下,終因蘇幫人多勢眾而獨霸一方。蘇幫獨霸書寓後,已無需競爭,書寓便漸漸放棄原先只賣藝不賣身的傳統而公開賣淫,這是在光緒十年(1884年)時的事情。書寓身價既落,必定招徠更多的下層人物光顧。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時,從事該行業的已達400人。雖然如此,由於傳統習慣的根深蒂固,進書寓的妓女仍需找介紹人推薦,並得學會幾句詞書裝裝門面。這仍讓人感覺手續繁,於是,一種身分與書寓相當,而無須履行這種繁雜手續的娼妓“長三”,便應運而生了。長三的出現,終於導致書寓在光緒末葉幾告絕跡。
長三
長三本來也是高等娼妓,只是自同治年間始,其取費規矩有了劃一的市價,以陪酒銀幣三元,留客度夜再三元而被人們從骨牌中的長牌六點圖案中演繹出來這一種稱呼。長三剛問世時,書寓朱素蘭等人不甘下風,將長三中有較高技藝的人挖過來開辦書寓,並使長三在相當一段時間中被視為下等娼妓。光緒末年,書寓被冷落,長三反過來又從書寓中吸收新人。
這時候的長三著手改革原先的收費制度,改為出局費一次一元銀洋,代辦酒席費每席十元,牌費每次二元。長三妓女和書寓一樣,亦標榜著賣藝不賣身,明裏不收過夜費,實際上仍是賣淫的。她們往往以添置衣飾、傢具等名目向嫖客索取費用,加上賞錢和點唱費等等,數目也很可觀。一般赴長三妓院一次,至少也要花去三五十元。長三妓院裏除了娼妓外,還有鴇母、司帳、跑街、廚司、車夫、娘姨、大姐、打底娘姨、打底大姐等,其中鴇母是妓院中最高權力者。長三中也有自願進妓院寄賣的娼妓和將身子押入妓院的娼妓。
早期的長三妓院,主要分佈在四馬路(今福州路)上的東西兩條薈芳裏,以後逐漸向三馬路(今漢口路)、六馬路(今北海路)發展。到1918年年底,上海的長三人數已達1229名,如果以每個妓女配有一至二名娘姨大姐計算的話,其從業人數之眾即可想而知了。
幺二
上海灘上還有一種被人們視為下等娼妓的“幺二”妓院。幺二的得名也同長三一樣,因其最早在同治年間的收費規定茶圍取資一千文,侑酒取資二千文,數目與骨牌中的三點相似的緣故。幺二的勢力在初創期時與長三不分上下,但由於居處、穿著和習慣遠遠不及長三,所以勢力日減,後又受到下等娼妓如野雞、臺基等的衝擊,身價日落,終於只能接納商店夥計和工廠工頭進院而淪為下等娼妓。幺二的地盤,起初只是在城北一帶,租界繁榮後逐漸移到公共租界的四馬路萃秀裏。為招徠生意,每年九十月間,幺二妓院門前還大排菊花山。光緒二十年(1894年)起至以後的十多年裏,幺二娼妓僅在東棋盤街一帶落腳,妓院的房屋大多為以前的客棧,十分簡陋。幺二的生活十分艱辛,往往在晚上六七點鐘吃晚飯時,才是來客最多的時候。妓女只需龜奴一聲“見客”,即刻到。
客堂裏站班聽來客挑選,被挑上的得強顏歡笑地應付一番,才能繼續回去吃飯,又得匆匆出來伺候客人,有時通宵達旦。不接客的妓女常是五六個人擠在一間雞籠似的小房間裏睡覺。據1918年6月統計,上海的幺二娼妓的人數達500名左右,由於環境和待遇惡劣,她們中患性病的人數極多。
臺基
光緒中葉(1890年左右),上海灘出了個綽號喚作白沙枇杷的蕩婦,此人首創癡男怨女集合的場所,名曰“臺基”。所謂臺基實際上只需租一間房間,招幾名願來這個場所的女子便可開張營業。來臺基的女子,多半是為與男子相愛而無法同居而煩惱的,白沙枇杷把這些人聚集在這裡吸引男子,坐收利潤。臺基中之上等者介紹一個女子收費銀洋10元至15元;中下等者只收5—8元。所收費用臺基主人取1/3,其餘歸臺基女子。約在1905年左右,上海務本女學的學生薛文華被學校除名後,便以女學生的身分作招牌,在五馬路(今廣東路)開設了一家駐顏閣照相館,遇見容貌出眾的女子便設法勾引來幹臺基營生。以臺基為形式的賣淫機關在上海灘曾風行一時。
野雞
清代咸豐年間(1851-1861),上海縣城內出現了又一種形式的娼妓——“野雞”,以後逐漸移到城外。
所謂野雞,實際上是以棲止無定的飛鳥為比喻的。隨著十里洋場的畸形繁榮,上海的野雞人數1918年達到6000人以上。其勢力範圍冠上海灘娼妓之首。
野雞被視作道地的下等娼妓,操這種生涯的娼妓,生活之苦是難以想像的。她們白天在茶樓賣笑,夜裏在街上拉客,不論夏日炎炎還是寒風凜冽,天天如此。往往是一個娼妓帶一二個娘姨,從夜裏八九點鐘開始,三五一群,八九一陣地在街頭伺機行事。
看準不是久居上海的外地人,上前便拉,形同劫持一般。有些初來上海的外地人見狀驚恐萬分,大聲呼救,有的還會拔拳相向。野雞娼妓有時一夜下來拉不到客,回家捱鴇母龜公拳打腳踢是家常便飯。更有甚者,野雞娼妓中尚有為數眾多的十三四歲未成年的女孩子,也在含淚操這種皮肉生涯。
野雞娼妓人數的眾多和活動範圍的廣闊,一定程度地影響了租界內的社會治安。每到夜裏,她們常常為了拉客發生幫與幫之間的爭吵,以及野雞和被拉客人之間的吵鬧。這樣一來,不得不使租界當局從原先的放縱變為干涉。
花煙間
光緒初年(1875年),小東門一帶還曾出現過“花煙間”,娼妓人數約200左右。先前,這種娼妓僅在城內虹橋左近出現,1874年因租界繁榮,便遷到城外臨河一帶。緊接著由於這一帶建造大量商棧,又向小東門遷移。以後,又進一步擴充地盤,在小北門附近發展,逐漸造成聲勢。花煙間娼妓大多是逃荒來滬的難民,或被惡勢力賣入妓院的女子。由於她們毫無人身自由,所以只得聽從鴇母龜公的宰割。每天天一亮就得在客堂間裏喊叫:“來哪!來哪!”接一次客只收費兩角錢,有時一天要接客十多次。花煙間接客的階層,基本上都是扛夫、水工匠、轎夫以及碼頭搬夫、人力車夫、工廠工人中無家室的青壯漢子。由於接客的人多而雜,因此花煙間娼妓幾乎人人都患有性病,通過接客又在社會上大肆傳播。花煙間妓女的收入全部交給鴇母龜公,在沒有客人光顧時,還得不停地做針線之類的活計,可謂艱辛之極。
釘棚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上海灘竟然還有一種比花煙間娼妓更為低下的“釘棚”。這些人多是花煙間和下等野雞娼妓中淘汰下來的,她們年老色衰,無路可走,全身患遍梅毒還得接客,一次收費先是制錢六十文,後來漲至一百二十文。釘棚娼妓的收入儘管十分低微,但鴇母規定她們每天須交納二元左右的費用才可完賬,否則便是無休止地打罵。釘棚娼妓先在香粉弄一帶活動,後移到棋盤街幺二妓院地盤附近。
鹹水妹
虹口一帶還出現過一種專做外國水手、大兵生意的粵籍娼妓,人稱“鹹水妹”。
“西妓”和“日妓”
舊上海還有一些外國娼妓,約可分“西妓”和“日妓”兩類。西妓主要是白俄和西班牙籍人,她們的活動地點以二洋涇橋為基點。日妓最初在白大橋北頭的三盛樓一帶活動,後來擴展到英法兩租界裏,它的前身為東洋茶樓。日本娼妓的一個特點是額外需索不苛求,以求歡為快,這便大大衝擊了野雞娼妓的營業。因為野雞的拉客對象與日妓相同,但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從客人身上大肆苛索費用物品。辛亥革命後,日本從上海召回日娼,才使這一競爭對手在上海漸漸消失。
娼妓業的廢除
娼妓業的興盛,必然會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道德觀念的淪落,語言的粗俗,思想、風俗的敗壞等等,給社會、家庭、婚姻帶來的弊端之深,是可想而知的。娼妓對社會無一利而有百弊,但在十里洋場之中何以能洪水猛獸般地發展呢?這個問題只能從主宰上海的租界殖民當局的立場,以及租界制度上去探究了。從眾多的資料中可以看到,租界當局在表面上是不贊同發展娼妓業的,而事實上卻以不聞不問的態度予以放縱。如果說租界當局曾提出過廢娼的主張,也全然是為維護其本國僑民或當局的利益而發起的。如《大陸報》曾發表過紀事,詳載上海娼業中的梅毒對美國水兵傳染的情況,要中外人士引起對娼妓危害的重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曾有過取締南京路和其他地段拉客野雞的行動,公共租界還成立過特別委員會淫風調查會,提出廢娼議案等,最終也只是議而不決,不了了之。
中國人在看到娼妓業的危害性後,倒做過幾件紮實的事情。如最初的濟良所,是專收不堪忍受鴇母虐待的妓女的避難機構,對娼業主產生過一定的抑製作用。又如1911年由紹興、寧波、湖州等同鄉會發起組織的全國婦孺濟救會,拯救過有志改娼為良的妓女千余名。此外,還有同仁輔元堂第六科的婦女工藝院,也使許多本來可能淪為娼妓的婦女得以謀生糊口。可惜此類機構基本上都是民間發起的,資金短缺,很難持久並有所發展。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制度以後,娼妓才得以廢除。 |
|